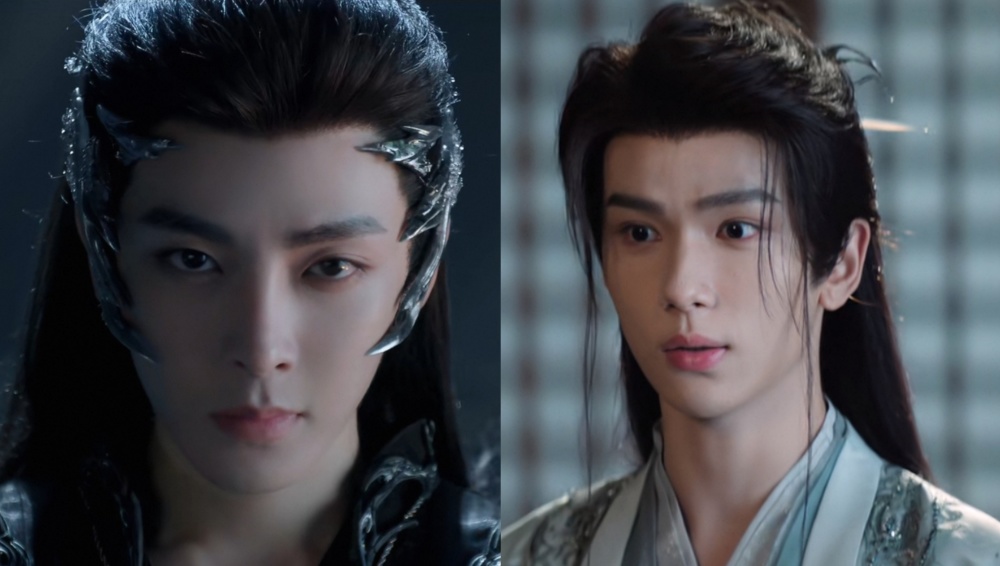正式加入東盟東帝汶總理流淚了
導讀:10月26日的東盟成員國簽署儀式上,58歲的東帝汶夏納納·古斯芒剛放下簽署筆,眼角的淚就砸在了印著東盟徽章的文件上。他抬手抹了下眼睛,旁邊的長趕緊遞來紙巾,卻被他擺手拒絕——鏡頭
正式加入東盟東帝汶總理流淚了
10月26日的東盟成員國簽署儀式上,58歲的東帝汶夏納納·古斯芒剛放下簽署筆,眼角的淚就砸在了印著東盟徽章的文件上。他抬手抹了下眼睛,旁邊的長趕緊遞來紙巾,卻被他擺手拒絕——鏡頭里,這位經歷過獨立戰爭的老人紅著眼眶笑,身后的代表團成員有的跟著擦淚,有的掏出手機對準簽字臺,連現場的東盟秘書長都輕輕拍了拍他的肩。
這一刻,東帝汶等了24年。
1999年全民公投脫離印尼時,這個位于努沙登加拉群島最東端的島國,GDP只有4.3億美元,全國像樣的公路不足100公里;2002年獨立當天,首都帝力的街頭還能看到戰爭留下的彈坑,民眾舉著用舊床單做的國旗,喊著“自由”卻不知道“明天吃什么”。2005年拿到東盟觀察員身份那天,時任總統拉莫斯·奧爾塔在記者會上說:“我們終于摸到了東盟的門,但要跨進去,得先讓自己站得穩。”
去年我跟著中國援東帝汶醫療隊去帝力郊區的貧民區采訪,賣水果的老太太瑪麗婭拽著我的衣角說:“我兒子去澳大利亞打黑工,三年沒寄錢回來,孫女的學費還沒湊夠。”那片貧民區里,孩子們光著腳跑,大人們坐在路邊發呆——東帝汶30%的人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,油氣資源即將枯竭,農業還停留在刀耕火種,“窮”像塊巨石,壓得所有人喘不過氣。
所以當“東帝汶成為東盟第11國”的宣言響起時,夏納納的眼淚,成了最直白的“情緒出口”。代表團官員奧古斯托·薩爾門托后來跟馬新社說:“我們哭的不是過去的苦,是終于等到了‘翻身’的機會。”加入東盟意味著什么?是能把島上的咖啡、腰果通過東盟自貿區賣去泰國、新加坡,而不是只賣給印尼商人賺“白菜價”;是能吸引馬來西亞的旅游公司來開發帝力的海灘,讓瑪麗婭的孫女有機會去酒店當服務員;是能參與區域經濟合作,讓這個“被世界遺忘的角落”,終于能蹭上東南亞發展的“快車”。
儀式結束后,我在會場外遇到了東帝汶大學的學生安娜,她舉著手機跟朋友視頻:“我們學校要和印尼大學合作了!以后我不用去澳大利亞留學,就能學國際貿易!”她的眼睛亮得像星星——對年輕人來說,“有學上、有活干”,就是最實在的“希望”。
東帝汶的“入盟路”,從來不是“求同情”,而是“拼實力”。這些年他們搞農業改革,引進中國的雜交水稻;搞基礎設施建設,修通了帝力到包考的公路;甚至把“減少貧困”寫進了憲法——他們用24年證明,“小國家”也能有“大決心”。
夏納納在儀式上說:“這不是旅程的終點,是新篇章的開始。”而這新篇章的第一頁,寫滿了134萬東帝汶人的期待:讓孩子有學上,讓大人有活干,讓這個“年輕的民主國家”,終于能在東南亞的地圖上,畫出屬于自己的“亮色”。
散場時,會場外的大屏幕還在循環播放簽署儀式的畫面。一位抱著孩子的母親指著屏幕說:“看,哭了。”孩子仰著腦袋問:“媽媽,他為什么哭?”母親笑著說:“因為我們的國家,終于長大了。”
風里飄來會場外賣的烤香蕉香,那是東帝汶最普通的街頭美食,卻帶著最樸素的溫度——就像這個國家的夢想,不宏大,卻真實:好好活著,慢慢變好。